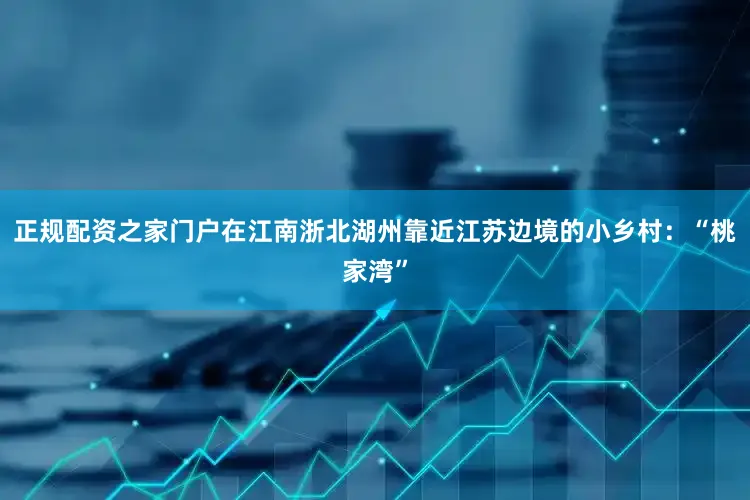
图片
舅舅是乡村教师
作者:邵国阳
我叫他:舅舅。但从我的经历来说,何以叫他舅,似乎很复杂。但不管怎样说,叫他舅舅,终归是对的。
舅舅的家,在江南浙北湖州靠近江苏边境的小乡村:“桃家湾”。小时候常去舅舅家,但他好像总不住在自己家里,多数时间是住在他那担任校长、语文老师、算术老师、又是体育老师的“桃家湾小学”里。
记得他住在学校的简陋宿舍里,屋里只有一扇破了的玻璃窗。透过那破玻璃窗,可以看见离小学校墙边三四步处,有一个河湾,河边有一棵桃树,旁边过去还是一棵桃树……是的,我舅舅是乡村小学教师。准确地讲当时应该还是个“民办教师。”那些年,在我的印象中,他来城里我家,一大半的事,是为了民办教师的转正。大概我父母亲是城里教育系统的干部,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,期望得到些内部消息和便利。
然而,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。舅舅也参加了多次转正考试,据他自己说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。但转正问题却是一拖再拖,只到改革开放后的七十年代末,八十年代初才真正转为公办教师。于是,舅舅在一次次考试,一次次失落中。继续在小乡村教个“复式班”拿村上的工分,课余还种田打理菜地。
至于,为什么他迟迟未能转正。后来才知道这和他的家庭出身及复杂家庭背景有关联。
我的外公(姑且这么称)解放前说好听点是乡绅,说准确点是大地主,好像还担任过类似保长的乡官。刚解放时因为对抗新社会,被收监后来处决了。所以,舅舅未能老早转正为公办教师,也就不奇怪了。
而舅舅是外公大老婆所生,却是外公的小老婆抚养大的。大外婆刚解放就不知去向了。而我和舅舅又没有血缘关系,这好像很复杂,但其实也简单。因为,我是从小过继给城里当教师的表姑妈,也就是舅舅的姐姐作儿子的。我的亲奶奶,就是外公的亲妹妹。但不管关系如何复杂,在我的记忆中,舅舅却是一个老实巴交,很有担当的好人。
说实话,我早先是不知道舅舅从教的具体情况的,直到八十年代,从父亲桌上的一本《教育通讯》中,看到了介绍舅舅的文章。才真正了解了他几十年坚守乡村教育的事迹。他一届届的学生升上中学、大学毕业。他虽然内心因末能转正,而有所委屈,但他仍在艰苦的条件下,“一个也不能少”的授教于乡村孩童,这种情怀有时想想真有些泪目。让我最切身感受的是舅舅,除了对乡村教育的执着坚守外,对亲情观念也是格外地浓烈。自然,对我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外甥,视为己出地疼爱自不必说,就说他对非亲生的母亲,我的小外婆的“孝道”。在村上也有口皆碑的。
小外婆顶了“大地主小老婆”的帽子,在当时的时代下,是抬不起头来的。而小外婆又没有子嗣,只有舅舅从小和她相依为命,后来,为她养老送终。
在小外婆在世时,我去看她。亲耳听舅舅,一口一个“姆妈”地叫着,且很自然很亲切,完全没有非生之子的感觉。小外婆去世时,快近九十多岁了。我记得她离世时,是带着笑容走的。大概她内心很欣慰。虽然,我从没见过面的外公,她的夫君无道。但这一生上天却落给她一个好儿子:我的舅舅。
现在舅舅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,但精神矍铄很健谈,回忆起历历在目的往事清楚的很。今年我去看他,见他还是乐观健康的状态,也很开心。但联想起最近网上讨论“教师八小时外额外付出”该不该的话题,真有些对舅舅他们那一辈基层乡村教师,坚守乡村教育的情怀,由衷地敬佩和唏嘘不已。感概良久,午饭后信步走出舅舅家门。门口那条小河还在,想起小时候每回寒暑假,舅舅摇着撸驾着船,吱吱吖吖地把我从城里接到乡下的情景,不由自主地从脑海中飘出一曲江南童谣:
“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,舅舅亲,外婆亲,还叫我是好宝宝……”
作者简介
图片
图片
作者简介:邵国阳,浙江省散文学会会员,湖州市作家协会会员。作品几百篇散见于:《江南》《辽河》《文存阅刊》《湖州日报》《三门峡日报》《浙江诗人》等报刊。
图片
图片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配资网平台,股票加杠杆网站,股票配资开户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




